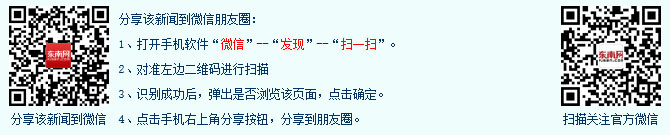“陆家山水”武夷情 叶礼璇/文 面对水清如玉的九曲、无势不奇的山峰,国画山水大师陆俨少激情难抑,吟诗道: “三三六六画堪诗, 临水登山事事嘉。 旬日武夷知不足, 不妨此地老烟霞。” “烟霞”者,“云气”也。武夷山的云气一入陆先生之画面,如挟风雷的动势顿时从宣纸上腾起,一破传统山水画之寂静、呆滞…… 确实,陆先生视武夷山水为知音者,这不难理解,自1956年起,四访武夷。第四次的访游,时逾半月之久。次数之多,时间之久,当代美术名家圈中陆先生当为首位。 1956年9月,作为上海画院中的佼佼者,陆先生被选为嘉定区人大代表,有更多机会饱览祖国山河,他选择了南下的线路,访游革命圣地井冈山后,抵达武夷山。 时逢雨竭初晴,山岚弥漫,茫茫云海中的群峰忽隐忽现于波涛 万顷之中…… 九曲水一碧如染,如玉带盘绕山中。山回溪折,折复绕山…… 充溢灵性的武夷山水——留在陆先生的创稿之中,或铅笔或钢笔勾勒…… 此时的陆先生已揉合南北二宗,初创出缜密娟秀之画风,灵气显露,变幻无方。 我以为是原生态的武夷山水为画坛大家的艺术生命注入了蓬勃生机。似无痕,然留迹。 回沪之后,陆先生为了让传统山水流传有绪,不绝如缕,有了编写一本关于山水画技法的书的设想。 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的陆先生白日在画院打杂工,夜晚下班,晚饭后在马路边路灯下,俯身小小方凳,从事写作,时常写到夜深入静…… 饱经风霜而坚韧顽强,令笔者遥想起屹立千壁上的天游峰雄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脱去“右派”帽子的陆先生及老伴偕刘旦宅夫妇一同到名山大川写生,于是有了陆先生的二游武夷。 1973年后,中美开始接触,周总理为了美化环境,迎接四方友宾,调一批画家到北京,为涉外酒店、宾馆作画。 文艺界松动的信号发出之后,陆先生调入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虽然未拿到正式员工的指标,但一年的两个假期还是让他欣慰。 1975年,陆先生利用暑假,第三次南下,直奔阔别十余载的武夷山。 上回尚在中年,此次已是老者。然而,未改容颜的依旧是那山那水……素朴一如往日的武夷山张开大臂迎抱画坛的这位虔诚艺术之子。 画家忘却了身负之荣辱,全身心地投入到武夷山水的创作之中,“留白”之风格得以发挥,宣纸上林木满山,云气缭绕,流水潺潺,留白处变化多姿,显现出了装饰美,“陆家山水”的美学价值初现于此。 陆先生1975年创作的山水册页之四为《武夷九曲图》,题款简约,仅有“武夷九曲闽游纪胜”八字。“九曲”被画家安排至画作左侧之一隅,而山峰则占据了绝大空间,山之色也并非“黑块”,而是有青绿夹杂其间。笔者推测,其时,变革画风之念头正在画家心中萌发…… 1978年5月创作的画轴《福建林区图》则还是保留画家原有的风格之作,溪流有放排情景,激流中可见排工搏击水浪之英姿…… 冰河解冻,春回大地。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巨大转折,陆先生的人生渐入佳境: 1979年1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陆俨少当选为协会理事。 1980年,陆俨少晋升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其后当选为浙江画院院长。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4年秋月,陆先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访游武夷山。年过古稀的先生尽管身份、地位非当年可比,但老画家一如往日的淳朴、敦厚、谦和。 其时,住在武夷宾馆的陆先生接到应约到北京为人民大会堂绘大型国画的电话,因而多留住了十余日。 多数时间,上午外出对景写生,午睡后作画,每每将画作夹挂于室内的铁丝上,随日增多,蔚为观止。 对陪同前来的友人,陆先生赠画表达谢意。画面的“江南早梅”,似乎不合当年的时令,然而拜读先生的生平有关文章、资料,使可得到合乎情理的答案。 陆先生的国画创作,以册页、手卷最为精堪。创作的《爱新就新册》便是其中之代表作。其之三为《闽峤林区图》题款为: “闽峤林区,予至福建,见其植被之厚而叹,林木之不可胜用也。当公路蜿蜒以进,依山傍涧,葱笼郁茂,林海广袤,数十里路无隙”。 “峤”在词典中解释为“山道”,是书面语,仅这一字可见大师传统文字功力不一般。 题款的结尾处为:“丙子俨少并记”一查年历表,笔者大吃一惊,靠近的,“丙子”年不是“1936年”即是“1996年”,前者不靠谱,而后者更大错矣,陆先生1993年就逝世了。显然老画家记时有误,名家也是人,犯错难免。如写“甲子”即1984年访游武夷之后创作倒是有可能的。有一画册中言,这是先生1975年的作品,这也是不对的。 八十年代初,陆先生已形成自家画风,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勾云”、“留白”、“黑块”的“陆家山水”,并有程式化倾向。 陆先生是有思想的人,他不想重复自己,于是心中酝酿着思变。离开武夷山,完成北京作画任务,回到杭州时他开始行动:他托人买来欧洲名家画集,同时买来外国的颜料,学习赵无级抽象油画章法形式。 当然他不会简单地跟赵无极走,而是按吴冠中说的“穿着大师的拖鞋走一走,然后把拖鞋扔了,在穿和脱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办法去尝试。 由于陆先生传统功力厚,加之思考能力超强,触类旁通,不久,便创作出了崭新的风格。 《闽峤林区图》中,画家保留了“勾云”、“留白”、“黑块”不见了,代之以“苍绿”,武夷山的大王峰巍然挺立,颇有气势。这幅画作,无论从构图、用笔,还是色彩与旧作大不同。笔者斗胆推测,此画正是陆先生革新画风时期的探索之作,至少留有变革的足迹。 在后来的《自叙》中,陆先生是如此回顾的: “翌晨即去武夷,住山中半月,畅游九曲之胜,上登天游,磴道依石壁而上,极为险峻。近望接笋峰,壁立千仞,径路斗绝,石级几不容足,奇险恐不在华岳之下。我常恨武夷不入画,自登天游,奇石嵌空,危峰回合,尽多粉本,而向之观看电视,参阅照片,皆不足据。”登天游俯看武夷山水胜境,大美如画,老画家创作激情迸发而出。 诗吟武夷事事嘉,醉写山水卷卷新。陆俨少先生的武夷之行令人时时回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