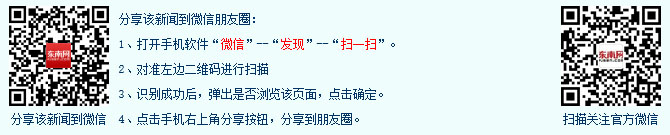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古镇里“老瓦头”,不知姓名,不知来自何方,不知居住何处,只知道老汉是泥瓦匠,有一手修砖墙、补漏瓦的好手艺,所以大家都称呼他为“老瓦头”。 武夷山的小镇,已有着千年文化历史。走在古街,一座座宋朝至清代的古民居、书院、牌坊、祠堂等古建筑映入眼帘。看去,巷弄相连,马头墙,黛青瓦的大宅,鳞次栉比、古朴庄重。尤其是那气派的节孝坊,留下皇恩浩荡与恩荣,顶着状元、榜眼、探花砖雕帽子的书院彰显着小镇的昔日辉煌,展示小镇的古典之美。 自小,我从古街的大石板蹦跳着去上学,小镇便印在心里。路面被车辙碾压出一道道岁月的痕迹,斑驳的青苔爬满砌得横平竖直的古老青砖,仔细地观察,从门墩到屋檐下都用砖石雕刻着精美的人物、花草、瑞兽等象征吉祥的立体图案,有破损的也被精心修缮过。 古镇建筑,让我看到一位修墙补瓦的老工匠--“老瓦头”。 我曾向爷爷奶奶问过这位大工匠,据镇里的人说,“老瓦头”是外乡人,不爱说话,可看见那些旧砖老瓦,他便双眼放光…… 小镇经历风雨后,就是“老瓦头”背着工具箱出现的时候。小镇的古建筑的屋顶均使用青瓦,青瓦是古代传统建筑中常用的瓦片,呈半圆弧片状,取自当地黏土制作后高温烧结而成,为黑灰色,通常是一凹一凸相互紧密衔接,整齐划一。凹者为阴面,凸者为阳面,雨落下汇聚到青瓦凹槽再沿着斜屋顶跌进墙角边小水渠里,像是一条条跳跃的水帘。不过,日子久了,一些老屋就会出现瓦片破损漏雨的现象,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装漏雨的锅碗瓢盆摆满了各处。到这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老瓦头。 早先,要见老瓦头要去老镇古庙去寻,后来只需到古街上唯一的老酒馆就行。当年,老瓦头经常着一身青色布衣斜倚在酒馆门槛旁的小竹椅上,头顶破了边缘的草帽,留着一缕花白山羊胡子,瘦削的脸颊随着他手中的竹烟枪烟火明暗而一张一翕,腰间常扎一条布腰带,脚上一年四季只穿一双黑布面纳千层底。他常常是让老板给他随身携带的酒葫芦里打上二三两散装米烧,那个年代的白酒,没有讲究什么品牌、包装,但是都是代代传承纯粮酿造,绝对正宗。再点上一小碟五香花生米,接着单手松一松衣领和腰带往那张他的专属竹椅上一斜躺,一只手举起蹭亮带着包浆的酒葫芦儿眯起眼仰头“嗞”的一声啜上一小口米烧,再伸出两根细长枯瘦的指头从摆在双腿上的小碟里夹起一粒花生米“呼”地一下精准丢进口中,从不失手。据他酒后吐话,他虽无亲无故、无儿无女,从小学泥瓦工,打石、砌砖、刷泥、垒灶,样样都会,而最拿手的工艺是修瓦补漏…… “老瓦头,修瓦补砖嘞!”有活儿的时候,来人只要往巷口一喊,老瓦头便来了精神劲儿,迅速起身,把酒葫芦往腰间一挂,扎紧腰带,穿好鞋子,正了正那顶破草帽,挺直身子大步流星迈下台阶,紧随着客户一道儿回家。 到了需要修缮的屋顶下,只见他先是背着手慢慢围着墙角绕上一圈,偶尔还侧身趴在砖墙上贴着耳朵仔细听着墙里的动静。接着踱步进屋,仰着头眯着眼仔细将正厅、天井、卧室、阁楼、厨房等处全部扫描一遍,心中便有数了。再根据观察得到的破损处需要更换的青瓦数量,用工具箱装上青瓦背在背后,一般一次不超过十片。来到墙角,两手紧紧一抓扶手“嗖”的一声,便麻利地蹬上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木梯,“刷刷刷”只三两步工夫便到了屋顶。那刻他稳稳站住,一手扶着箱子,抬起头弓下身,两只眼睛像锐利的鹰, 踮着脚尖轻轻踩在日晒雨淋墨色的青瓦上,那些薄脆的瓦片偶尔在他脚下发出轻微嘶哑的呻吟,三两步来到需要更换的破损处,左手固定住上层瓦片,再伸出右手细长瘦削的指头,只一钳一提,破瓦便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取了出来,再将身后箱子里的新瓦稳稳地补到破瓦处盖好,紧接着修补下一处,还顺手将屋顶堆积的树叶、杂物清理干净,以防积雨。他在屋顶轻盈跳跃犹如灵活的猴儿,却从不曾踩坏一片瓦。有些有难度的诸如四角天井、屋脊、攒尖、封火墙顶等处的缺损青瓦也难不倒他,经过他一番妙手修补过的屋顶能保管十年都不会再漏雨。老瓦头名声,传出周边乡镇。 平常没活儿的时候,他就兀自坐到酒馆打烊,老板也任由他,数十年如此,在两人心中已经形成一种默契。待老板将要关门时他便起身系上酒葫芦,趁着夜色消失在小巷里。 最后一次听说老瓦头是他在给城东开米铺的李老板家补瓦时,一不小心从十几米高的隔火墙上跌落身亡。常言,身落吾乡即乡亲。李老板便和村里乡亲张罗着给老瓦头厚葬。神奇补瓦匠的一生就此落幕,令人唏嘘。 如今我每次回老家,常会抬头看看那些墨色的青瓦,脑海里总是浮现那个身背工具箱轻盈跳跃在各家屋顶的熟悉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