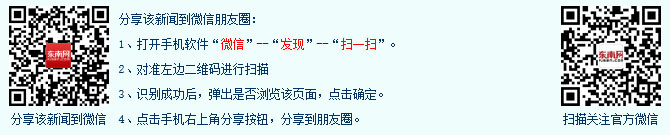在中国道教史上,白玉蟾可以说是罕有的天才人物。他不仅是南宗金丹派的实际创立者,同时也是南宋文坛上彪炳一时的奇才。无论在道教理论与实践方面,还是诗文书画领域,都达到相当的高度,从而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一生云游,踪迹遍布江南,而对他最有意义的地方,则是武夷山。
云游入山
白玉蟾第一次到武夷山时,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衣衫蓝缕,蓬头垢面,打着赤脚,形象极为狼狈。关于这次的云游,白玉蟾若干年后在《云游歌》中有过相当具体的描述:
身上衣裳典卖尽,路上何曾见一人。初到孤村宿孤馆,只有随身一柄伞。
囊中尚有三两文,行得艰辛脚无力。满身瘙痒都生虱,茫然到此赤条条。
思欲归乡归未得,争奈旬余守肚饥。炎炎畏日正烧空,不堪赤脚走途中。
一块肉山流出水,岂曾有扇可摇风。黄昏四顾泪珠流,无笠无蓑愁不愁。
偎傍茅檐待天晓,村翁不许住檐头。……
白玉蟾原姓葛,名长庚,祖籍福建闽清。祖父考取功名后,即往海南琼州任教职。后因祖父、父亲均逝,母亲改适白姓人家,故改姓名。白家亦是书香门第,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得白玉蟾从小就受到良好文化教育,再加他个人的聪颖天份,七、八岁就能背诵儒家六经,算得上是“神童”。十岁时,前往广州应童子试,取得优异成绩。为了测试他的才学,考官额外要求他以“织机”为题作一首诗,白玉蟾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
此诗气魄宏大,锋芒毕露,让人难以相信出自一个孩童之口。考官大概是个保守的冬烘先生,当场将他刷了下来。原本恃才傲物,对考试抱很大期望的白玉蟾,受到极大打击。自此不再留意功名仕途,转而云游江湖,求仙问道。
宋代延续唐代游侠之风,民间好讼,且好斗轻死。所讼之事多为冤曲之事,或者贫者为富者兼并,或者弱者为强者所害,或者愚者为智者所败,横祸飞来,逼人已甚,官府腐败,无处鸣不平,只得寻求剑侠帮助。因落第而心有不满的白玉蟾,毕竟年少气盛,对世道与仙道的理解并不深刻,曾花了不少精力去学习剑术。可以想见,他最初所求的仙是“侠仙”。
剑法年来久不传,年来剑侠亦无闻。一从袖里青蛇去,君山洞庭空水云。
逸人习剑得其诀,时见岩前青石裂。何如把此入深番,为国沥尽匈奴血。《习剑》在一些有关白玉蟾的记载中,曾经提到他“任侠杀人”一事。然而究竟为何杀人,所杀者是谁,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只说到当时在江湖引起很大反响,而他为了逃避官府追捕,不得不隐名埋名,到处云游,形同乞丐。
白玉蟾云游到建宁府所辖的武夷山时,那些道观道士见他又脏又臭,又没有道士度牒,将他拒之门外,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痴坐九年
白玉蟾再次入武夷山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道士了。这次到武夷山后,整整痴坐了九年。
此时的他,已经得到明师陈楠(字翠虚,外号陈泥丸)道法秘传,在江湖上有了一定名声。但行踪不定,多以癫狂形象示人,故世人多不识其所谓“痴坐”的真相。事实上,白玉蟾的“坐”,并非象达摩面壁一样合十枯坐,而是终日握拳闭目;“痴”,则是像年少云游时一样,依然一袭长满虱子的破衣,蓬头赤脚。有时发足狂走,有时整天酣睡,有时长夜独立,有时酒醉终日,有时哭,有时笑;只有最亲近的弟子才知道,他是以异于常人的痴颠方式炼丹修道。
除了痴坐外,白玉蟾与当时武夷山的许多人都有交往。其中最密切的当属时任武夷山冲佑观观主的苏森与女道士刘妙清师徒。
苏森系苏东坡后人,自号懒翁。或许是秉承家风吧,懒翁三教兼通,神清骨朗,风度不凡,白玉蟾一见就为其打动。当即作诗以纪:
一掬精神迥出尘,懒翁自是不凡人。渊明松菊迳犹绿,灵运池塘草正春。
坡仙何日跨鲸归,公是苏家老白眉。把剑舞残杯内酒,抚琴弹破笔头词。
懒翁见了白玉蟾后,也为他的气度才情所吸引。自此后,白玉蟾时常到冲佑观与懒翁叙谈,饮酒,品茶,并有多首诗呈懒翁:
荷笠欲寻懒翁去,带些爽气入疎棂;懒翁老白结忘年,秋入淡烟疎雨天。
醉把黑甜圆个梦,时将草圣放些颠;杖藜还尽溪山债,杯酌结交风月缘。
……
旋开白酒买莲房,满泻桐膏炤玉缸。月女冷窥青斗帐,风神轻撼碧纱窗。
公疑我是今皇甫,我恐公为昔老庞。醉后唾珠粘纸面,笑将笔力与人扛。
懒翁亦有许多诗文回赠白玉蟾。在《跋修仙辨惑论序》中,懒翁说他与白玉蟾“一见如故人”,盛赞白玉蟾的诗文,“方寸一点浩然,发为词翰,已无烟火气;一丈草书,龙蛇飞动,诗章立成,文不加点”;披读白玉蟾的《修仙辨惑论》后“知先生骨已仙矣”,认为白玉蟾将“处心积虑,有意度人,与前贤不侔”。
懒翁对白玉蟾的认识,可谓深刻。他并不那种只为自己长生久视的炼丹求仙者,而是有着普度世人情怀的大仁大德者,完全可以许多前贤比美。
刘妙清是浙江东阳人,年少时貌美,见者莫不心动,不幸而沦落风尘。年长后猛然醒悟,于是辗转来到武夷山,拜道士陈丹枢为师。其时陈丹枢在武夷五曲云窝铁象峰上结茅修道,年已八旬,鹤发童颜。白玉蟾曾有《云窝记》《题丹枢先生草庵》等诗文描述过相关情景。刘妙清说明前来求道之意后,陈丹枢对她说:修道居住在岩谷,生活非常艰难,因此学道非常难。刘妙清听了之后回答:“粗粮可以为稀粥,破布可以为衣服,野菜可以吃,薯芋可以煮,只要有个存身之地,就可以搭茅棚,采浦兰编蓑衣,骨柴之火可以煨食;父母没有生我之前,寒暑不知道,枯骨火化后,不再诉饥肠。如此,辨道应该可以吧?”陈丹枢听了笑说:“入道容易,如同穷途末路的猿猴投入树林;叛道也容易,如同水中游鱼跳跃上岸;道之在心,即心是道,你如果能有终有始,就是幸事啊。”于是收留刘妙清为徒。此后妙清自已动手割茅草盖了一间茅屋,附在陈丹枢茅屋旁,取名为“棘隐堂”。并请白玉蟾为之作记。
在《棘隐堂记》中,白玉蟾叙述了刘妙清出家修道,亲手搭建棘隐堂的经过后,感慨万千地写道:
取名棘隐,盖取名何仙姑所谓幽居山林间,荆棘隐此身之句。青松翠竹,潇洒倏然,唳猿啼,寒烟漠漠,风魂月魄,潇洒无际,此棘隐之乐也,夫棘隐之中,其所用心者何如哉。……学仙非为难,出法离欲为甚难哉,神仙长生久视之道既可学也,则出尘离欲夫何难之有。刘妙清既如此用心,则必可望也。
詹琰夫,亦是白玉蟾时常交往的道友。詹琰夫字美中,崇安人,世代官宦之家。因为感叹世事清浊混乱,故而入山修道,喜欢井灶丹汞之术。得知白玉蟾到武夷山之后,仰慕其人,倾其家财,寻得止止庵旧址,重新建立新庵,延请白玉蟾入庵主持。白玉蟾以兴未尽婉拒,詹琰夫请求他云游归来后,一定来永身居住。白玉蟾为他诚心所感,终于答应了詹琰夫的请求,并作了《重建止止庵记》。在文中白玉蟾追溯了止止庵的历史,描述了止止庵及周边风景后,深有感概地阐发了“止止”对于修仙悟道的意义。在他看来,“止止”即止于当止。止在易象中为山,山高峰险,不可盲进,故引申为停止。修仙悟道,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养意,即摒弃世俗名利,既入武夷山,就隐于山,止于山,乐于山,忘于山。甘过俭朴生活,使心灵回归本来之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成就大道。
今天人们在参观游览止止庵时,仔细玩味白玉蟾的止止释义,依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人生和事业的启示。
碧芝靖社
正是这个重建的止止庵,使得白玉蟾的晚年有了一个稳定的道场,跟他学道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便在止止庵旁设立了一个讲道传业的专门场所,命名为“碧芝靖”。
所谓的“靖”,又称“净室”或“静庐”,原是汉晋以来道教天师道在家设立的静室,专供祭祀祈祷,传道授徒的场所。因为净室是诚心之所,故与其它房屋不相连接,开门关门,均应轻手轻脚,室内只摆香案,香烛,桌案,书刀四物。白玉蟾参照净室布置与功能,将学生组织起来,自创了一个门派。
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宗教意义的道教,诞生于东汉顺帝、桓帝时期。到南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以正一,上清,灵宝三大派为主的符录派。符录派以南方巫术为其重要思想来源,长于斋醮祈禳之术,最典型的就是今人常见的香港影片中捉鬼驱妖、呼风唤雨的道士形象。除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自称为独得异传的神霄派,专以神霄雷法驱风唤雨,降妖除鬼。神霄雷法以融合符录与内丹为特色,主张内炼为外用符录之本,强调祈禳灵验的关键在于运用自身的元神。但这一派的传承主要是依靠师徒间的私相授受,直到白玉蟾才建立庵观,组成教团,制订教规,行符设醮,传丹法和雷法,正式形成道教南宗金丹派。
白玉蟾一生收徒极多,知名的有彭耜、留元长、叶古熙、赵牧夫、詹继瑞、陈守默等,而且都有著作文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得意弟子彭耜(字鹤林),他所撰的《海琼玉蟾先生事实》,完整准确的记录了白玉蟾的生平经历。这些徒弟,又广收徒弟。元代时,还有建宁人翁雷室擅名东南,从者数百人,时任建宁儒学教谕的赵菊也入其门下,将白玉蟾的教派与道法广为弘扬,从而产生广泛的影响。
白玉蟾在武夷山时,还曾为武夷精舍塑朱子像而奔走化缘。曾有学者认为白玉蟾在武夷山期间,朱文公也在武夷山。朱文公晚年对道教丹法经典〈周易参同契〉产生极大兴趣,但因其中隐语太多,百读不得其解,很想请教白玉蟾,然终因放不下架子而未能随愿。有弟子问为什么白玉蟾有神通,而老师没有?朱文公则以“偶中耳”回答。实际上,这只是一段戏说而已。白玉蟾本身就比朱文公年纪轻,痴坐武夷山时朱文公已逝世十多年。两人根本无从谋面。但对很早就通晓儒释道三家的白玉蟾来说,对朱文公的理学也有深刻的研究与理解。在他心目中,朱文公的形象十分高大,因此在游武夷精舍时,看到曾经一度高朋江座,弟子盈门的精舍,开始颓败冷落,仅余一幅青苔剥落的朱文公画像,怀着对朱文公的敬仰崇敬之心,写下了《朱文公像赞》:
皇极堕地,公归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鸣蝉。
又写了《题精舍》:
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前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
随后,为塑朱文公像写了《化塑朱文公遗像疏》:
武夷文公精舍欲塑文公遗像,不知当时抠衣者如之何则可。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雨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已草,文公七十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说。
在化塑文中,白玉蟾对朱文公的极尽推崇,甚至将其比之于孔子第二。今天这尊文公塑像早已无存,然而白玉蟾所写的诗文却留传了下来,印证了两位大师在武夷山的一段隔空佳话。(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