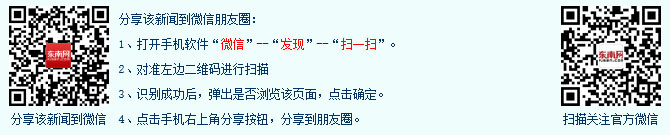武夷茶是福建最早见诸于文赋诗词的茶类,千百年来,品评、研究、吟诵武夷茶的文化积淀十分丰富厚重。武夷茶最早文献的探讨也一直在深入,作者在编撰《武夷茶经》和《武夷山市茶志》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新的观点和论据,现整理出来,供读者讨论。 一、武夷茶已被认知的最早文献 目前研究认为武夷茶最早记文为宋朝陶谷撰《荈名录》中收录的《晚甘侯》、“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云:晚甘侯十五人,遣待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践用之。”(见《中国茶文献集成》第二册76页)。孙樵,关东人、笃于学、工散文,大中九年(公元855年)登进士弟。丹山碧水为武夷山别称、唐时崇安未设县属建阳。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孙樵、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职方员外郎。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述评》著作中同意新志中就此推断:孙樵的茶文“先徐夤的茶诗约七十年,武夷茶最古之文献其在斯乎。”(见吴觉农《茶经述评》,318页)。 《全唐诗》七百零八卷收录了徐夤《尚书惠腊面茶》。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园、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飞赠恩深最知异,晚铛宜煮北山泉。”徐夤(公元849-921年,莆田人),唐末学者,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士弟、授秘书省正字。《全唐诗》共收录徐夤诗245首,《尚书惠腊面茶》是其中之一,是吟诵武夷茶最早的诗作,也是目前发现福建省最早的咏茶诗。 二、还在研究的武夷茶早期文献 北宋词人孙渐的《智矩寺留题》记述了四川茶祖吴理真引建溪茶种植于蒙山顶,被立碑,《名山县志》收录了碑文,其中有“昔有汉道人,薙草初为祖。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至今满蒙顶,品倍毛家谱。紫笋与旗枪,食之绿眉宇。”追记了汉代道人(吴理真)引武夷山区建溪茶种,种植于四川蒙顶的茶事。(见程启坤《蒙顶茶》16页)(《武夷茶经》卷九,294页) 宋代苏轼撰《叶嘉传》,以拟人写法,记述汉武帝喜欢“叶嘉”,歌颂武夷茶,文中记“叶嘉、闽人也……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天子见之曰,吾久饫卿名,但未知其实耳,我其试哉!……由是,宠爱有加。”(《武夷茶经》卷十三,491页)。在这里苏轼把武夷茶引伸到汉代,因未见其他文献记载,目前作为传说。但是汉武帝祭祀武夷君却是记载在司马迁著的《史记》中,武夷山闽越王城遗址,出土了类似茶壶的汉代的陶盉,也是例证。 清代蒋衡撰《晚甘侯传》,记述:“晚甘侯、甘氏如荠、字森伯、闽之建溪人、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先是森伯之祖,尝与王肃善及肃入魏而见辱于酩奴。”(《武夷茶经》卷十三,509页)。王肃(公元454-501年)北魏琅琊人,癖与茗饮。陆羽《茶经》中茶之事《后魏录》:“琅琊王肃、仕南朝、妤茗饮莼羹。及还北地、又好羊肉,酩浆。”人或问之:“茗如何酩?”肃曰:“茗不堪与酩为奴。”蒋衡在这里记述武夷茶“森伯”的祖先曾经被南朝王肃喜爱,而王肃是在南朝“茗与酩为奴”屡载茶史的一段公案的主角,因此茶学大家陈椽据此推算武夷茶最早被人称颂可以追溯到公元497-502年间(见《武夷茶经》卷十四,614页),这个推算也待其他史料佐证。 三、笔者考证认为,南朝江淹是武夷茶最早记录人。 江淹(公元444-505年)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学家,他约在公元473年由东海郡丞贬到到吴兴(现今浦城县)任县令,公元477年又被朝廷召回,后官至中书侍郎。江淹在他的《江文通集·序》中对这一段经历写到:“地在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至爱。不觉行路之远,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见《历代名人与武夷山》,62页),这段序文、记录了江淹在吴兴当县令时(约在公元473-476年)受建安郡丞陈昱等邀请,到早已向往,传说武夷君的武夷山游览经历。武夷山,地在吴兴东南峤外,闽越王城旧境内。江淹对武夷山“碧水丹山”的赞美吟诵从此成为武夷山的代称,千古传唱,明朝建文年间“碧水丹山”还被刻在九曲溪的水光石上,点悟着历代游客。 笔者认为这段记文中还有一个重大信息,被长期忽略了,这就是被南朝时江淹平生至爱的“碧水丹山”山水外,还有“珍木灵草”,“灵草”就是江淹记述的武夷茶,也是他平生至爱。茶叶在古代称谓很多,如“荈”、“茗”、“荼”、“苦茶”皆从草,也称“灵芽”、“灵草”。“茶”字为唐代陆羽著《茶经》前后开始通用,固定下来。 把茶称为灵草,自江淹后各个朝代都有。在记文,诵诗中把茶称为灵草,或者把武夷茶直接称为灵草的列举部份文献,如:唐朝陆龟蒙的《茶人》:“天赋识灵草,自然种野姿。闻来北山下、似与东风期,……”(见《全唐诗》); 北宋黄庭坚的《碾建溪第一》:“建溪有灵草,能蜕诗人骨。除草开三经,为君碾玄目。……”(见《武夷茶经》卷十二,423页);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十四):“予山居有茶论,尝茶诗云:谁把嫩芽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风吹一寸长。 元朝赵孟頫的《御茶园记》:“武夷,仙山也。……,爰自修贡以来,灵草有知,日入荣茂。”(《武夷茶经》卷十三,496页); 明朝、罗廪《茶解》“而今之虎丘、罗齐、天地、顾渚、松萝、龙井、雁荡、武夷、灵山、大盘、日铸诸有名之茶,无一与焉,乃知灵草在在有之。”(见《中国古代茶叶全书》,275页); 明朝许次纾的《茶疏·产茶》:“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唯有武夷雨前最胜。”(见《武夷茶经》卷十三,498页); 清朝蒋周南的《咏茶诗》:“丛丛嘉茗被岩阿,细雨抽芽簇实柯。谁信芳根枯北苑、别绕灵草产东和。上春分焙工微拙,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买,楚材晋用帐如何。”(见《武夷茶经》卷十二,473页)。等等 以上是各个朝代将茶和武夷茶称为灵草的部份摘录,也可印证南朝江淹早在公元473-475年间游览武夷山,赞美碧水丹山,欣赏珍木,品饮灵草,不觉路远,还与道书为偶(武夷山为道教十六洞天),或日夕忘归。江淹提到碧水丹山、灵草,与唐末孙樵提到的“丹山碧水”, “晚甘侯”,与清蒋衡提到的“晚甘侯,字森伯、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森伯之祖,与王肃(南朝)善”都存在一定的联系,甚至是相互呼应的。也佐证了江淹是用“碧水丹山”来描写的武夷山水,用“灵草”来描写的武夷茶最早记述人。江淹至爱的“灵草”就是武夷茶,他在《江文通集·序》中关于灵草的记文应当是武夷茶的最早文献。 如果这一考证被茶界接受,武夷茶最早文献将由此前认知的唐代孙樵《晚甘侯》文的时间往前推至南朝,提早330年。(肖天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