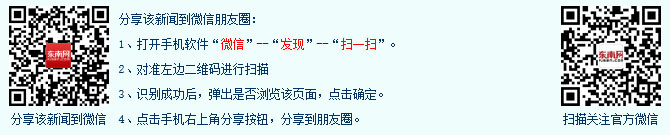|
上述可知,朱熹把理与气看成是构成万物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有理有气,万物方生。但二者又有区别,理是形上,是本,是无形,只能感知;气是形下,是末,是有形,可以直观。 3、不可变易性。理的不可变易性来自于理的客观性、形上性,换句话说,理的客观性、形上性决定了理的不可变易性。因为物是客观的,而理又是物之理,当然也是客观的。 理的不可变易性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区别事物是此事物,不是彼事物)、状态(以何种方式存在)、变化(如何演变)、发展(向何种方向发展)。在朱熹看来,万物之所以发育,就是因为理发生的作用,归根结底是由事物的性质发生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朱子之理被视为客观唯心。 (二)、陆九渊之心的哲学架构 朱子之理是物质基础上的理,也就是物之理。陆九渊以心为理,在朱子之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心,或者说在物、理之前安置了一个心,从而构筑起一个物、理、心的哲学架构,成为宋代以心为先、以心为本的哲学命题。 朱熹强调客观之理,而陆九渊则不同,他以心为理,强调主观之心。在他看来,心是主宰天地的主体,只有发挥心官的作用,才能体察天地之理。其心论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1、主观性。陆九渊之心,概而言之就是以心为先,在他看来,天地之间以心为本,只要心在,天地就在,万物就在。我心即天地之心,我心即万物之心,所以要以天地之心为心,以万物之心为心。如果我心不在,天地不存,万物不存。可见,陆九渊以心为先、以心为上、以心为重。他从“宇宙”二字得到启发,提出了“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58](《陆九渊集》卷三十六),把心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具有主观性。 必须指出,陆九渊同样没有否定客观物和物之理的存在。虽然陆九渊不言物之先、理之先,但从他的话语中仍然可以看出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至少他强调的是心与物、心与物之理同时并存。他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59]√(《宋史》卷四百三十四)陆九渊把宇宙与我融为一体,我之事就是宇宙之事,宇宙之事就是我之事。可见,陆九渊没有把至明的人与宇宙相隔裂,而是在客观物和物之理的前提下强调要物我观照。基于心的主宰作用,陆九渊很关注作为万物之灵的个体与宇宙的关系,要人用我之心观照宇宙之心。他说:“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60](《陆九渊集》三十四) 在陆九渊看来,宇宙是客观存在的,而我是苍茫广阔宇宙中的一份子,置身于这个空间的我要思量如何与宇宙同为一体,我之心如何与宇宙契合,如何做一个有利于宇宙循环、万物生生的人。可见,陆九渊视我之心为宇宙的本体,万物都是由我之心派生出来的,这是陆九渊至明的精神境界。 2、可变性。与朱子之理不同,朱熹强调客观之物和物之理,人必须体察客观之物,更必须体察客观物之理;而陆九渊淡化了物和物之理,强调的是离开物和物之理外的心。这是陆九渊之心与朱子之理的本质区别。 物、理、心三者须作两段看,物、理一体,有物有理,理寓于物,都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变的客观世界;心则存之于我,更操之于我,是可变的。心的可变性,是因为心容易受喜怒哀乐情绪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容易受到利益的驱使。心的可变性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