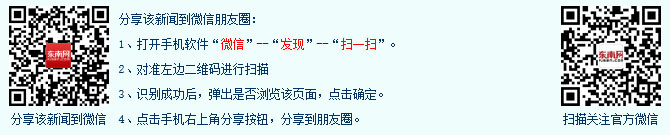|
理寓于物,要识察物之理,必须细察于心,有个知觉处。朱熹说:“天下之物,至微至细者,亦皆有心,只是有无知觉处尔。且如一草一木,向阳处便生,向阴处便憔悴,他有个好恶在里。至大而天地,生出许多万物,运转流通,不停一息。”[91]朱熹认为心与理会通,要发挥知觉的主动性。知觉是客观事物进入人的感官通过大脑的作用感知事物。如它的存在、性质、状态、变化、发展,都可以在感知的召唤之下得出结果,从而得出事物的整体表征。可见,朱熹不仅承认心的作用,而且也承认陆九渊说的有心才有物,有心才有理。反过来说,如果无心,何以有物,何以有理。 朱熹认为心有两面性,在内为性,在外为理。他说:“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92]“心唤做性”是就本体言,等于承认陆九渊的以心为本,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事唤做理”则是心的外用,是心的表现形式。在朱熹看来,天地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清有浊。可见,朱熹既把心视为万物之本,又把心视为体现理或天理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心的作用是“知”,要以心之知感物之理。朱熹认为,万物都有知的功能,只是它们知得狭窄,他说:“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93]而人则能知全体、知万事万物,这是人与物的根本区别。 朱熹认为知在我,理在物;知是主观,理是客观。他说:“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94]“宾”与主相对,就是客观。朱熹强调主观与客观要统一,以我之知悟物之理。朱熹还认识到客观之理无穷无尽,知也无穷无尽。朱熹明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有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95]要让客观之物和物之理存之我心,必须主客合一,才能穷究事物之理。今天我们把朱熹的理学看成是唯心论,并且曾在相当一个时期对此妄加批判,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出朱熹完全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朱熹还告诉人们要常常唤醒良知良能,去体察客观之物和物之理。他说:“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唤醒。”[96]朱熹认为人要明理,必须通过格物,让心致其知。他说:“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97]致知要发挥心的作用,心不正则无法观物,更无法识理,即便识得物和物之理,处事也会出现偏差。朱熹就认为载沉载浮、载清载浊、载驰载驱,全在人之心意。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评判:“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 [98],这是逆人之心;“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99]这是中庸之心;“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100]这是偏执之心。三者以中庸之心最为可观。 致知在格物,读书也是致知的一种方式,而读书也必须用心。朱熹说:“盖为学之事虽多有头项,而为学之道,则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101]朱熹用自己治学的实践教育弟子。他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102]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以理为本,是他认识世界的哲学思路,但这条路径也与陆九渊之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通过心的作用,察“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103]因为朱熹说的理既含盖宇宙,也含盖社会人生,是自然规律和社会的准则,他说:“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104]有时候,朱熹也把道视为理,他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105]由此可知,朱熹不仅强调理,也强调心对理的作用,更把理引入社会人生,而人生之理是万物之理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