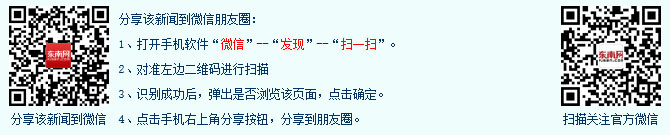|
韩国西江大学郑仁在教授将朱子学传入韩国后的发展情况,区分为“本源朱子学”(比较符合朱子的学问)和“修正朱子学”(与朱子学说有一定差异的学问)。罗整庵是“修正朱子学”的鼻祖,李栗谷深受罗整庵的影响,属于修正派。李退溪反对罗整庵,属于本源派。郑仁在理解的朱子学,是指朱熹之前的北宋五子之学、朱熹本身思想,及其在中国、韩国、日本、欧、美的发展与修正。这是一种广义的朱子学概念。 东亚朱子学是东亚儒学相关论述与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指出,近七百年来东亚各地儒者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绕开朱子。从东亚儒学的发展来看,朱子(晦庵,1130-1200)之学涵盖了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相关的儒学拓展、传承与研究呈现出两个层次的特质:第一个层次是儒学由中国经由韩国向日本的传播过程中,有着共同关切的典籍(例如《论》、《孟》)与议题(例如“五十而知天命”、“四端七情”、“民贵君轻”等),而对议题的发挥程度与内容则彼此不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学价值理念在“同心圆”式的逐层展开时,呈现相当的类似性;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各国朱子学思想内容在类似性中展现其殊异性,也是“理一分殊”之具体而微的表现。但是经典与议题的同源性和类似性,不能强制规范各区域的分殊表现,因而这里便涉及到第二层次的“去中心化”现象。就各区域文化发展的多元以及民族或政治之自觉而言,日韩儒者极不愿将中国儒学视为其唯一中心,而中国儒者也不能一厢情愿地将日韩儒学看作其附庸或边陲。“中心—边陲”的论述很难解释这类文化与思想的发展轨迹,即以希腊和基督教文明的发展为例,西欧与美洲大陆日后的发展,已取代这两种文明起源地的重要位置而成为新中心;而佛教在东亚与南亚的特殊发展,亦早与印度佛教分道扬镳,并在后者衰亡之后成为新的思想与信仰的重镇。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 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 ,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我们认为,东亚朱子学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朱子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本源的朱子学,也必然包含本源的朱子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正确立场是“中国本位,东亚视点”,或者“中国本源,东亚视点”,注重东亚朱子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区分东亚朱子学的不同表现形态。东亚朱子学是“一体多元”的朱子学,“一体”指朱子学说本身,“多元”指朱子学在东亚的不同的发展形态。 二、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提出,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早在700多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此时的朱子已经是走向了世界。近年来,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东亚朱子学研究者逐渐正视中、日、韩和欧美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将自身定位在“国际朱子学”的脉络之内,密切关注同领域的研究动态,对相关学术资讯的把握相当及时而准确。如何面对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中国大陆朱子学界整体直面的重要课题。“面对”即意味着吸收与批判,而日本、韩国学者在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长期积累与贡献,更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展开东亚朱子学研究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