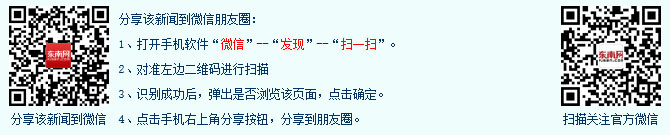|
难以想象,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出身竟然是一介布衣,生前几乎没有什么“功名”,最后朝廷按照科举特例,“特奏恩迪功郎”给予进士,并着任安溪主簿,未及到任,却以65岁享龄病逝。他“赋姿纯朴,颖悟过人,自少即高自期许,不同流俗”。年青时,听从好友忠告,从事圣贤学问以代举子业。读了朱熹与吕祖谦的《近思录》,把周敦颐、陈颢、陈颐,特别是朱子作为自己人生楷模,努力学习和践行他们的思想。也许是时代安排或许命运的造化,他曾两度聆听朱子的教诲,在漳州和建阳任上和任后,他们演绎了一段师生同道的佳话。学生说:“十年愿见而不可得。”老师曰:“吾道得一安卿(陈淳字)为喜。” 朱子与陈淳几乎是同道之友,教学别具一格,常常或是诸生皆退,留淳独语;或诸生入侍彼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说;或召诸至卧内,首问“安卿更有甚说法?”《朱子语类》一一七卷记载“训淳”三十四条,共计万余字,是朱子与门人对话中最多的。胡适先生有言:“陈淳二次的记录最小心,最用功,最能表现朱子说话的神气,是最可宝贵的资料。”陈淳两次求学,终于实现了“上达下学”思想认识上两次飞跃,所以他成为朱子最得意的四大弟子之一,因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只得通过学界交流中寻觅,向专家们去请教。我请来了叶明义先生和郑晨寅教授,前者是三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的具体参与人,后者是福建师大国学方面的研究生。话题围绕陈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展开。他们用四个字概括了“北溪先生”的历史作为——“理学津梁”。陈淳毕生对朱子理论进行了最准确和最权威的诠释。美国学者狄百瑞认为,几乎没有什么理学概念和范畴未列其著作之中,且“篇篇探心法之渊源,字字究性学之蕴奥”。其阐述精辟而又系统,是理学入门的钥匙,后人称为“东亚第一部哲学辞典”。 朱子去世后,心学兴起,陈淳不遗余力地捍卫醇正理学,对陆学大加挞伐,以至于后人对其批评太过略有微词。坚持师道发展师道。曾称赞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全祖望,在《宋之学案·北溪学案》中说陈淳“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他完成了从门人到传人的转变。不只是朱子思想的再解释,同时,条分缕析,融会贯通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是诠释,又是构建;是继承,又是创新。加上他在浙江、漳泉一带讲学,既开当地风气之先,又培养一批批弟子门人,因而被标举为“紫阳别宗”。因为他的历史贡献,清雍正二年(1724年)被配祀孔庙,成为孔子之后2000多年来全国172位享此殊荣的贤哲大儒之一。 《陈淳评传》近日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泰山学者”曾振宇先生领衔、海峡两岸十几位对陈淳素有研究的学者参与撰写,历时三载,主要从“陈北溪生平与著述”以及“理”“道”“太极”“仁”“孝”“释老”等为题,从二十四个儒学范畴、观念入手,对陈淳思想进行深入探析,既是陈淳研究的一大创获,又可视为思想史研究范式的一次新的、有益的探索。 只得从民间考察中寻觅,向百姓去了解。我走访了北溪书院、龙文实验小学,市井生活不少场所,验证了厦大高令印教授所说的一番话:“陈淳之学,是成熟心智、健全人格、安身立命之学。”陈淳反复强调,圣贤学问“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皆是“人生日用人事间”之事。再深奥的天理,最终都体现在人生日用之间,生活伦常自有其天命、天理的根源,尽人事处即为天理,因此要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