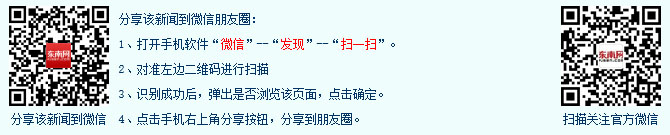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一)新理念 朱熹直承孔孟,把孟子关于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宗旨,阐释说“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一句话,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向善,不仅是个体人格的完善,还要使社会性集体人格完善。《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儒家的“三纲领”。朱熹注释“亲民”解为“新民”,也就是要求社会精英们在自己拥有高尚德行后,还要引导全社会明德善行,不断追求至善境界,造就一代又一代新的社会有用人才。朱子规划了圣贤君子培养的“路线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儒家所谓的“八条目”。在这个发展链条中,“修身”是“内圣外王”的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也是教育的全部价值所在。其哲学依据可从朱熹的理气论和人性论上进行说明。“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统一于天理,“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这样,他就在理一元论的前提下,构建了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使道德教育具有了本体论依据。由此推出“性即理”,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前者是天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本质,后者则是人的特殊本质,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但“性可复”,性发而情,“心统性情”,“只是这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是善,人心“可为善,可为不善”,只要主敬涵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变化气质,就能人心变道心,止于至善,成为圣贤君子,成就天下大业。 (二)新学校 朱熹的教学活动既重官办学校,更与私立书院关系密切。史志记载,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亲手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撰记题诗7所、题词题额的6所。钟情书院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朱熹可谓第一人。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代。如果说唐代的书院只是作为官学的补充,那么朱熹的教育实践则赋予书院全新的内容,邓洪波教授撰写的《中国书院史》指出,书院规制在北宋就已经形成,但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却是朱熹完成的。朱熹将书院规制扩展为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问六大事业;朱熹制定了书院的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出了“圣贤所以与人人为学之大端”,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揭物之要,朱熹还编写刊印了系列教材。 由于书院大多由民间设立,国家虽有支持和褒奖,但其经济和办学思想是独立的,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书院就大大有别于官学和一般私学,书院教育主要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有着自身的学术师承。书院不是单纯的师授生学的被动学习,而是以学生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会讲、师生讨论、学生切磋等教学形式,十分注重“对话”学风的发扬,追求极大的自由精神。书院有教育更有教化,强调德行的圆满,人格的完善,心灵的满足。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道天,由人文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教育一项重大目标所在。”书院不同于官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它是对科举考试的修正和批判,也是对教育宗旨的正本清源。虽然通过书院教育不乏金榜题名者,虽然朱熹本人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且他的著作后来作为开科取士之制,但他却是科举考试的坚决反对者。朱熹在《信洲洲学大成殿记》文中说,“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学问。”在《答腾德章》信中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且技愈精,其害来愈甚。”朱熹极力主张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既不同意当时宰相赵汝愚的“三舍法”,也不赞成其他人提出的“温补法”。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州县共同承担选拔人才的责任,要求以德为先培养人才,选拔敢于承担大任而有实学者。朱熹对科举考试的批判是严厉的,甚至直斥士子“钓声名,干利禄”,“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成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这就是朱熹为什么热衷于兴办完全不同于官学教育路线的书院的原因。 (三)新教材 朱熹捍卫道统,又发展道统,思想解放疑经惑传,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中国古代教育经典内容,在汉代是“六经”,汉代以后除去《乐》称为“五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五经”对大一统的国家意志指导不强,与释老抗衡的针对性不够,也不利于士子学人循序渐进地学习。朱熹与时俱进地以《四书》代替“五经”,使中国古文化主题鲜明,体系完整。《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而《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临死前三日还在改写《大学·诚意章》的注释。1182年,朱子在浙东任职上第一次将“四书”刊印,并第一次提出“四书”之名,在武夷书院教学期间刻印了“四书集注”。朱熹认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为。”朱熹认为学习儒家著作,要先“四书”后“六经”。“《四书》,《六经》之阶梯。”而就《四书》体系的内部而言,朱熹主张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来学习,道理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朱熹关于教材的革新是成套、系统的,将士子个人的“学”与为公众的制度的“教”加以沟通,考虑到儿童与成人、普通人与统治者的不同教育特点;注意到不同学者的水平差异;也考虑到了课程教材结构的平衡;兼顾了儒家经典的重新编注与中心的突出;关联了经典的学习和新近的学术,特别是新儒学的发展,这样就为新儒家教育理想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学者狄百瑞把这一套新的系统化的教材列为十一项,即:1、《小学》,作为学习的最基础的教材;2、《乡约》,广涉乡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交际规范;3、朱子公告类(如《谕俗文》)《晓喻词话谍》《晓谕居表持服遵礼律事》等),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地方事务及人际活动的指导;4、《白鹿洞书院揭示》,基本的学校教条;5、《朱子家礼》,家庭生活礼仪与传统礼仪;6、《四书集注》,反映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与理想;7、《经筵讲义》,为统治者所谈基本讲义;8、《近思录》,《旧书》入门及成圣贤之序;9、《伊洛渊源录》,新儒家的学说本源;10、《通鉴纲目》,修正《资治通鉴》,立正统正人心;11、《学校贡举私议》,所有为学之要旨。 (四)新方法 钱穆先生言,“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 朱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他说,“道有实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共性个性统一。朱熹总结了孔子的教学方法,在有教无类,同等教育前提下因材施教,因人培养。朱熹的门徒众多,年龄不同,知识底子不同,禀赋、兴趣也有差异。他根据各人“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他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 教育学习相长。朱熹根据《礼记·学记》所说,“学,然后能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又引用孔子和子贡问答,要求师生在教学中都能日新其德、共同进步,而且指出,教是仁,学是智,对己对人都是高尚的。基于此,“学不厌”“教不倦”。基于此,朱熹对学生采取诱导为多,而不仅仅是授受。朱熹对学生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去思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用商量而已。”基于此,朱熹要求学生多多向教师提问。《朱子语类》中记载的门人所提的许许多多问题,都得到朱熹的详细回答。朱熹提倡师生之间相互问疑,“学贵有疑”,“疑而后问,问而后智,知之真则信”。他们经常在夜间就着烛光进行问答讨论,仿佛像“夜大学”。 致知笃行并重。朱熹十分注重学习的实践性,并要求理论联系自己。他所说的“知行相须”如此,“博文约礼”也是如此。他指出,“致知力行,用功不何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知行相须,有如眼睛和脚的关系。当然学贵践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方面的用语,朱熹多有强调,如力行,践行,躬行,践履等,朱熹把读书与其功夫论结合,要求与自身修养联系起来,“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但恐用意不精或贪多务广,或得少为足,则无由明白”。用现代人的话语,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所说的践行,也包含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一生提倡“崇德进业”“成就德业”“措诸事业”“因于世用”“经天伟地”的实学。 课里课外结合。朱熹注重课堂常规教学,既有师道尊严的一面,又有营造轻松气氛的一面。喜欢用生活中熟悉的事例和画图讲解书本知识。著名的解《易》图就是,以图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既浅显易懂,又生动活泼。朱熹还把课堂延伸到室外,举行讨论,辩论和会讲,同时带领学生游历灵山秀水,放怀吟唱。“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其门人叶贺孙说:“及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千古绝唱《九曲棹歌》就是在武夷书院办学期间写就的。 (待续) |